
从上周开始看朱莉亚·格拉丝的小说《三个六月》,现阶段的我还停留在保罗思绪飘飞的希腊之途中。只是今天我离开了希腊,注意到的却是封面上的那句话:“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,实际上就是我们心中原本想要去的地方。”提醒我重新注意这句话并且难以离开视线的是刚刚收到的soho小报里的两篇文章。一是冯唐的《择一城而终老》,二是刘苏里先生推荐陈之潘《剑河倒影》的《“国土沦亡,根着何处?”》。冯唐最终没有做出回答他择了何城而终老,感动我的只是题目。而刘苏里先生文章里引起我注意的则是另外一本书封面上的句子(李零先生的《丧家狗》)“任何怀抱理想,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,都是丧家狗。”文字是一处曲径通幽的风景,我从《SOHO小报》里进去,从《三个六月》离出来,看到的无非是“我们想要去的地方”。
我们要去哪里?是肉体欲望的驱使?还是精神家园的指引?
我们该去哪里?能去哪里?
冯唐用看似调侃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也许有些严肃的问题,择一城而终老看似大象临终前的寻觅。而我想的似乎又过于现实,择城而居?我们本就居住于一城一处一地一方。我生命的
 大部分居住在江南的一个小镇,大部分青梅竹马的伙伴们生于斯,长于斯,也会终老于斯。几万人口的小镇或许对我来说太小了,某对夫妻的枕边风估计没有几日就能吹到山的另一边去。城市和人的双向选择淘汰了我和家乡小镇的居住关系。在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,我漂浮在中国的城市间,从南到北,从东到南,除了遥远的西部还未曾涉足。南京街头繁密的法国梧桐让呼吸的空气充斥着植物的排泄物,成都光膀子壮汉的体味夹杂着麻辣兔头的余香,深圳快步疾行的人们眼睛里闪烁着霓虹灯的反光,……我一路走来,却总是在城市的十字路口迷路,何去何从,东西南北,总是想,即使能跟着一条迷路的狗也好。李零先生描述的丧家狗该是如此吧,至少乌纳穆诺曾经这样写过。或许对我来说,这些城市永远都是太大了,上海话蔑称中的“乡下宁”该就是指我这种出身小城镇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吧。大,太大了。
大部分居住在江南的一个小镇,大部分青梅竹马的伙伴们生于斯,长于斯,也会终老于斯。几万人口的小镇或许对我来说太小了,某对夫妻的枕边风估计没有几日就能吹到山的另一边去。城市和人的双向选择淘汰了我和家乡小镇的居住关系。在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,我漂浮在中国的城市间,从南到北,从东到南,除了遥远的西部还未曾涉足。南京街头繁密的法国梧桐让呼吸的空气充斥着植物的排泄物,成都光膀子壮汉的体味夹杂着麻辣兔头的余香,深圳快步疾行的人们眼睛里闪烁着霓虹灯的反光,……我一路走来,却总是在城市的十字路口迷路,何去何从,东西南北,总是想,即使能跟着一条迷路的狗也好。李零先生描述的丧家狗该是如此吧,至少乌纳穆诺曾经这样写过。或许对我来说,这些城市永远都是太大了,上海话蔑称中的“乡下宁”该就是指我这种出身小城镇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吧。大,太大了。我该身栖何处?过小的家乡难禁我的跨越,过大的都市难辨我的方位,不大不小?
“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,实际上就是我们心中原本想要去的地方。”说不清是什么指引我,基于爱情,基于一种停留的渴望。我来到了奥胡斯,这个丹麦的第二大城市,这个坐落在日德兰半岛东海岸的“世界上最小的大城市”。如果照冯唐衡量一个城市丰富程度的四个标准,这里该是一个适合他终老的城市。在这个46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既可以欣赏到13世纪建成的Domkirke(圣克莱蒙的大教堂)辉煌,
 也有丹麦著名建筑设计师安·雅各布森设计于1941年建成的市政厅;
也有丹麦著名建筑设计师安·雅各布森设计于1941年建成的市政厅; 既有集合了来自全丹麦75座古老城市建筑的Den Gamle By(老城——记录城市文化和发展史的国家级博物馆),
既有集合了来自全丹麦75座古老城市建筑的Den Gamle By(老城——记录城市文化和发展史的国家级博物馆), 又有不时定期展示来自全世界艺术品,本身也是一件建筑艺术品的Aros。
又有不时定期展示来自全世界艺术品,本身也是一件建筑艺术品的Aros。 至于时间,这个最小的大城市交通便利,从郊区到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半小时,何况还有世界上几乎最守时的公交班点。至于人,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文化背景甚至不同性取向的人都是这个城市的30万分之一,尽管也有白眼和冷遇,但是大多数陌生人见面时的问候就是微笑。这适合冯唐的最终选择,不过这是否就是我的最后一站?我该终老于此?
至于时间,这个最小的大城市交通便利,从郊区到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半小时,何况还有世界上几乎最守时的公交班点。至于人,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文化背景甚至不同性取向的人都是这个城市的30万分之一,尽管也有白眼和冷遇,但是大多数陌生人见面时的问候就是微笑。这适合冯唐的最终选择,不过这是否就是我的最后一站?我该终老于此?还没有答案。至少现在还不知道。于是,我依旧还需要看着远方的帆船,测试着风向,关注着天气。我的理想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,我依旧还是一只丧家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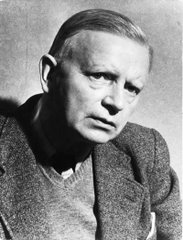
Ingen kommentarer:
Send en kommentar